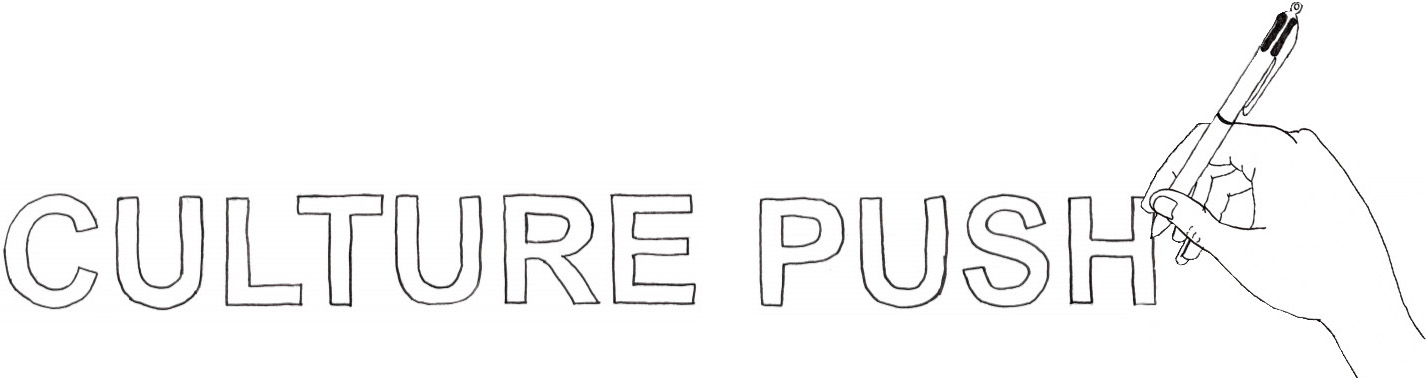還劍湖,河內,越南。攝影/陳慧瑩
海外離散華人的真實: 這一年,一個人的世界旅程
陳慧瑩
這一年,我去了八個國家的唐人街,對離散與家園概念進行了跨國性的調查。作為衛斯理學院肯那佛(Knafel)計畫學人,我自己獨立規劃了這趟四大洲的旅程-秘魯、古巴、南非、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及中國,考察了每個國家獨特的華人移民史以及最終成形的唐人街。選擇這些國家的原因,是因為它們有著淵遠的移民歷史-自19世紀初,即有成千上萬的苦力搭船抵達該處-還有我個人的研究興趣。我通常以唐人街為起點,再循線探索該國的歷史及現今的移民社群。為了追尋家族在中國的根源,我見到了一群七十歲高齡才開始學中文的華裔古巴奶奶們,並記錄了許多移民遷徙的故事、韌性及變化中的族群與認同。以下是五個主題、反省與心得收穫。
1. 全球草根運動的影響
原住民土地權利運動,雪梨,澳州。 攝影/Elaine Syron
我離開美國時,仍是巴拉克歐巴馬擔任總統的時候。我在哈瓦那住處的客廳目睹唐納川普入主白宮,之後我即持續探討川普對海外社群的影響。去年八月,我第一次聽聞三K黨在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集結,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在雪梨初次接觸原住民黑權運動。澳洲奴役制度所奴役的對象是十九世紀時的原住民及太平洋島民,而1960年代的原住民黑權運動從美國的民權及黑權運動中得到啟發,以原住民自決為中心而構築的運動,在數十年後終於取得一些勝利,例如成立了原住民法律諮詢機構,原住民醫療機構以及社區教育中心,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群島島民仍持續組織並關注拘留中死亡、縉紳化、土地權利及結構性不義之補償等議題。白澳政策,在20世紀通過一系列保持澳洲白人移民及英國化的法令,反映著美國於此之前的反移民政策,如1882年排華法案,時至今日,這兩個政府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延續著相同的政策,在馬努斯島拘留中心內的暴行,以及美國政府仍拒絕通過正式的夢想法案等,都是其中一例。這些相似性使我明白,西方帝國在通過系統性的壓迫政策彼此會直接相互影響。然而,過去、此間、其後的抵抗與運動卻也一樣堅強。從原住民黑權運動、雪梨紅坊區到紐約哈林區堅強的草根組織,不論主流媒體是否報導,人民對彼此之間產生抗拒及影響也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從澳州「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到全國性原住民所領導的氣候正義運動,運動能量正火力全開。
2. 變遷中的族群:華人作為壓迫者或被壓迫者?
與海外華人社群共同生活時,我接觸到勞工階級移民在異國的各種故事,但也看見同一群人操著同樣的種族歧視修辭。反省亞裔美國人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的角色後,我更加理解就華人如何被歸為有色人種這件事,其實是眾說紛紜,且完全是社會建構的。華裔友人曾問我:「我們算是棕色人種嗎?」,也有朋友寫下了「沒有所謂”華人”的正義」一文,即使我們看起來有所選擇也是一樣。
Chinatow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攝影/陳慧瑩
旅行過程中,我見到華人確實可能因為身處的國家、歷史脈絡以及他們的政治傾向,而成為壓迫者或被壓迫者。當我比較了自己在古巴及南非的經驗後,就看得更清楚了。哈瓦那的唐人街是一個主要為黑人的社區,混居著年長的古巴華人,包括非裔華人的後代,許多具有百年歷史的華人協會組織也聚集在那兒。另一方面,約翰尼斯堡則有著長遠的種族歧視及種族隔離歷史,當地的南非華人主要是單一族群聚居,部分原因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使然,縱使在南非已歷經數個世代的華人,仍生活在主要為華人的社區裡。我拜訪了兩個約翰尼斯堡的唐人街,聽到許多反黑人的情緒性言論,一些南非華人已內化地認為歷史上的種族隔離有其必要。種族隔離的歷史讓人們根深蒂固地認為,努力變「白」同時意味著追尋更高的自由。見到如此固著的種族主義想法以及兩國間極端的差異,使我更加明白種族真真切切是一種社會建構。就像在美國的華人族群-特別是單一族群聚居者,會因為種族問題而集結起來,然而令我感到不安的是,這樣的模式已遍布世界各地,但在美國「亞裔支持黑人活命」運動中,卻看不見相同的動員能力。
3. 找尋家園
與秘魯華人年輕人聚會,並分享紐約唐人街經驗。利馬,秘魯 /攝影 Jorge Augusto Chang
在利馬的前幾天,辨認當地貨幣、公共交通以及瞭解單身女性如何安全地旅行等事讓我極為忙亂,當我終於抵達唐人街時,掛在餐廳櫥窗內的烤鴨、店鋪口販賣的糕點以及小時候熟悉的超市零嘴,喚起了家的感覺,讓我再次記起為什麼自己會選擇來到這裡。無獨有偶,我在廣州時,來自迦納的友人也和我分享了相同的感受。當他第一次到廣州時,他的朋友帶他到小北,一個位於市中心、人稱小非洲的地方。移民們多年來在此建立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鄰里,並有著繁盛的商業活動,他的朋友也帶他到可以安頓下來的社區。即使族群飛地正在經歷全球性的變化,這些地方仍讓許多人找到了家。
我與離散社群的人們越來越親近,因為我們都有著追尋超越地理性概念「家園」的欲望。我與一群秘魯華裔年輕人成為好友,他們充滿好奇地彼此分享、交流對於在一個國家發展出家系世代一事的想法。對他們而言,同時身為華人及秘魯人,需要一個意涵更廣泛的詞語,才能將混血族群身分認同的複雜性呈現出來。他們稱自己為tusán,源自中文的「土生」(tǔ sheng),意思是在當地出生。聚會時,像是發現華人食物秘魯化的過程,竟與其美國化的過程相同,還有土生認同運動的快速發展,都讓我們共同感到驚嘆。跟他們在一起分享故事、笑聲,在中國餐館咬下第一口食物時,我找到了家的感覺。我提醒自己要相信這個過程,這些與他人心靈相通的時刻都是在因緣際會下觸生。
4. 以酷兒、性別意識及非二元化的華裔美人姿態,生存及探索世界
還劍湖,河內,越南。攝影/陳慧瑩
其實這並不容易。在家鄉,縱使身處騷動混亂的美國,我都有一個彪悍的酷兒及跨性別亞裔美人社群能給我慰藉,他們是我的堡壘。然而在這一年當中我學到,為了生存與持續旅程,我必須在當地紮根,而非一直仰賴家鄉的人們。這一年來,我並沒有對大多數人公開自己的酷兒身分,幾乎所有人都只認知我是個女人。有一段時間,異性戀與順性別是全球擋也擋不住的性規範。在某些國家,因為我在種族及性別上被劃歸為單身、年輕的亞洲女性,街頭騷擾甚至特別猖獗。順性男會是第一個對我吹口哨的人,言談間充滿侵略性,或對我的研究主題夸夸其詞地說教。進行家族尋根研究時,我最終找到一本與我家族同姓的族譜,但只有男系子孫的名字能被記載在上頭。因為我不是男兒身,也不能傳承家族姓氏,所以無法得到人們同等的尊重。雖然我身上流著強悍女性的血液,並且來自一個有色人種學生會教我如何悍衛自我主張的女子學院,但我仍有脆弱的時刻,我因為自己存在及成立的方式感到十分孤單。
然而,深入挖掘自身的力量,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社群。在秘魯,我遇到一位酷兒,他教我西班牙語在殖民地發展出來的中性詞彙,例如todxs 及amigxs (朋友),這也成為我們在whatsapp 上交談的共同語言。在越南,我從臉書聯繫到河內酷兒(Hanoi Queer),一個常為酷兒社群舉辦聚會的團體,並參與了他們的活動。在中國,我見到傳統村里文化下的異性戀婚姻,使婦女犧牲自己只為了養育子女、操持家務,不禁使我深思,先祖輩的酷兒們是如何撐過來的。相信在殖民統治前,一定存在著幾世紀之久的酷兒文化,即使無法浮出檯面,但卻彰顯在今日人們的行動中。
5. 日常生活的韌性
母親的故鄉,泰山,中國。攝影/陳慧瑩
經過多年來在亞裔美人組織工作者社群的洗禮,我對何謂一個運動者有著清楚的理念與定義。然而,我在旅程中拓展了自己對行動主義的理解,發現其意義更加包羅萬象。在古巴,有許多中國移民在1959年古巴革命後逃離,留下來的人不是因為相信新政府就是因為他們無法離開。我遇到一些祖父母輩的長者,他們曾經歷那段歷史,而為了維持唐人街的存在,他們仍持續運作華人組織,縱使許多華人機構早已消失了。有些中文班的學生已經超過七十歲了,他們生平第一次學習中文,只為了與自己的傳統有所連結。我回到我的祖父母們在中國的故鄉,認識了那些曾與祖母一起在水稻田裡耕作的老奶奶們。文化大革命後,這些女性仍留在當地,健康地活到高齡,從中國父權及貶低女性勞動力的體系裡生存下來,她們從來沒有用過「行動者」的字眼。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我遇到因生存迫切需求而組織起來的伙伴,他們沒有任何資源協助。聽他們分享華裔馬來西亞人在唐人街如何保護社區並抵抗都市化迫遷,我震驚於他們的故事,與紐約、舊金山及波士頓唐人街反縉紳化的故事竟然如此相似。
回到紐約,日後,當我思考如何與在傳統意義下政治語言及抗爭想法都不同的人們一起參與運動時,我將記取這些日常行動的抵抗與韌性所教我的事。這趟旅程給了我希望,在不同的流亡時刻,華裔長者在公園裡跳舞、下棋、玩牌,同時間也有著成千上萬的集結正在發生。這樣的想法已足夠支持著我繼續前行。
攝影/陳慧瑩